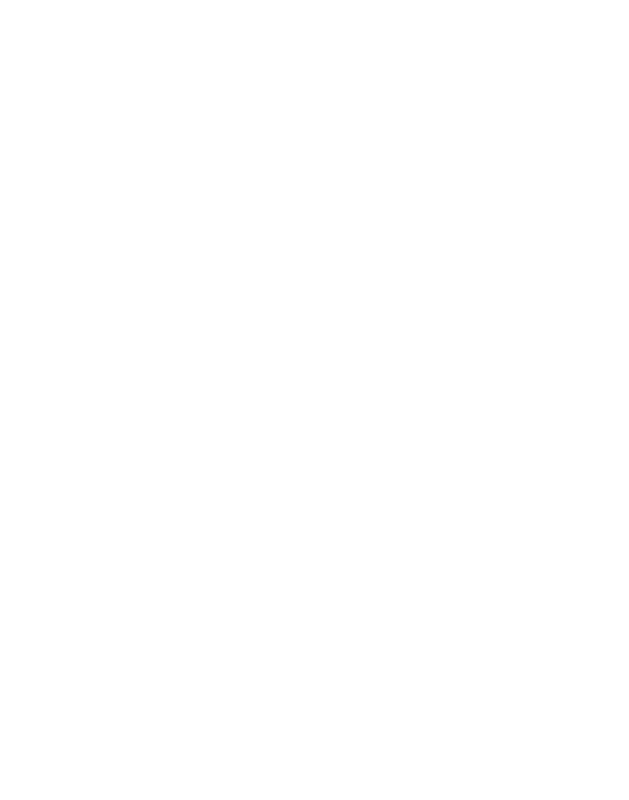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的交响音乐。中国交响乐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交响乐;中国交响乐的形成;民族特色;马里奥·帕奇;朱践耳。
ISSN:2972-4201
ISSN:2972-4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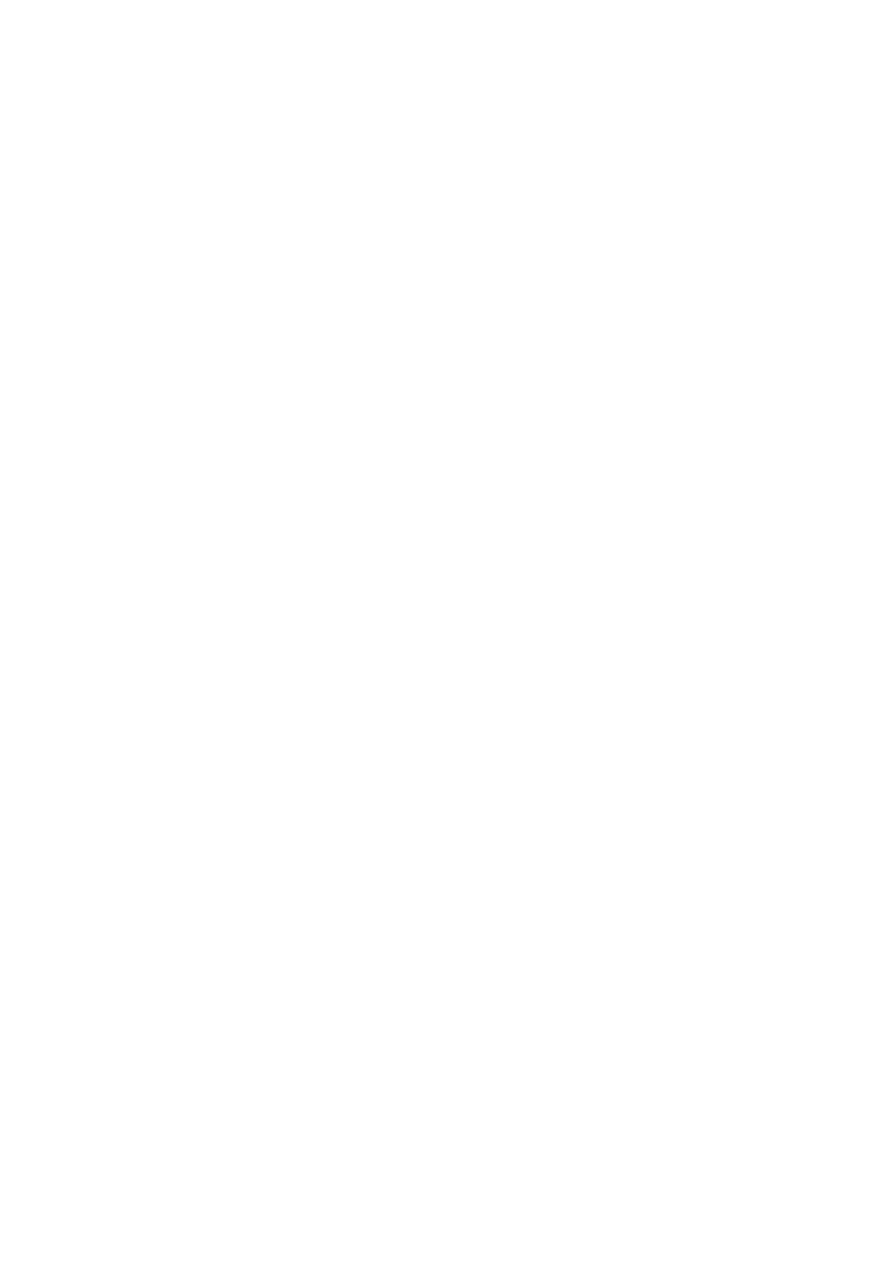
《现代教育论坛》2024 年 8 期刊登,国际出版刊号 ISSN:2972-4201
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的交响音乐。 中国交响乐的形成与发展。
库琴科·塔拉斯耶维奇-库岑科,张家界学院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湖南张家界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e-mail: terryheimat@gmail.com
说明
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响乐的发展为例,探讨了亚太地区交响乐发展的历史轨迹。内容包括:中国交响乐的发展阶段;中国交响乐的形成;将交响乐引入中国文化的实践;"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以及交响乐与国家京剧院的纵向结合;第一批交响乐团的历史以及指挥家在中国交响乐团曲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国交响乐文化发展的一些代表人物传记。
关键词:中国的交响乐;中国交响乐的形成;民族特色;马里奥·帕奇;朱践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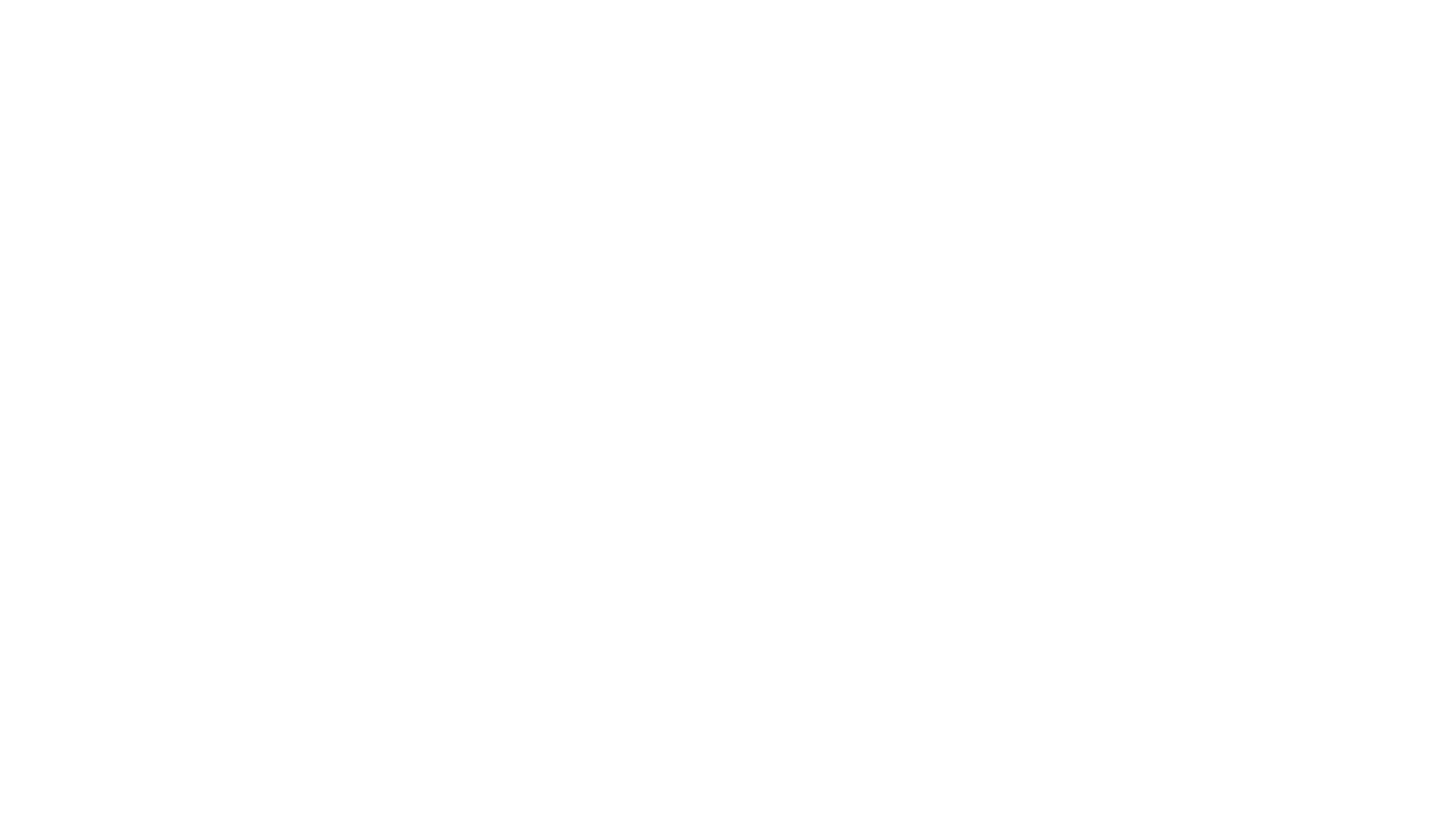
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大理石浮雕。9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浮雕描绘的是由 12 名乐师组成的宫廷乐队。所有乐师都是仕女,面容丰满,体态肥胖,颇具唐代特色。右边是乐队的指挥。右下角是两名身着中亚服饰的舞者。
序言
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历经了一条从管弦乐创作到逐渐绽放出民族交响乐独特魅力的渐进式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交响乐积极吸纳了世界交响乐的创作精华,于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出其独树一帜的特色。对这些特色的深入研究,使我们得以构建一个清晰的历史年表,从而揭示出中国民族交响乐发展的质变轨迹。
20世纪的中国音乐艺术以其创造性发展的鲜明特点而著称,其中,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无疑成为了推动中国音乐不断前进的旗舰力量之一。虽然交响乐并非源于中国,但它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蓬勃发展,无疑成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生动例证。这种交融不仅强化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国家象征意义,更彰显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卓越水平。中国历来秉持博采众长的开放态度,同时也不吝与世界分享自身的文化遗产。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正积极探索音乐文化与交响文化的发展空间,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正迈向更加和谐共融的新境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功构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交响乐体系,而这样的成就在西方音乐史上往往需要几个世纪的积淀。进入21世纪,中国交响乐已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概念和特征,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亚太地区,更是跨越国界,响彻全球。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某种不健康的“主次分明”刻板印象的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对于中国交响乐的报道与研究仍显不足。在多数情况下,它往往仅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一个章节被提及,而未能得到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文化生活的历史和社会学背景紧密结合,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其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中国交响乐发展历史的系统梳理与深入论证,构建了一个详尽的历史年表。这一年表不仅揭示了交响乐形成的动力机制,更凸显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特色与成就。
中国交响乐发展阶段
1930-1950年无疑是中国交响乐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组织管弦乐团,并涌现出第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管弦乐作品。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国内军事动荡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先进社会力量的进步活动(如载入史册的“五四运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交响乐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意大利著名音乐家马里奥·帕奇(梅百器)的领导下,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交响乐团。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正式起步,并为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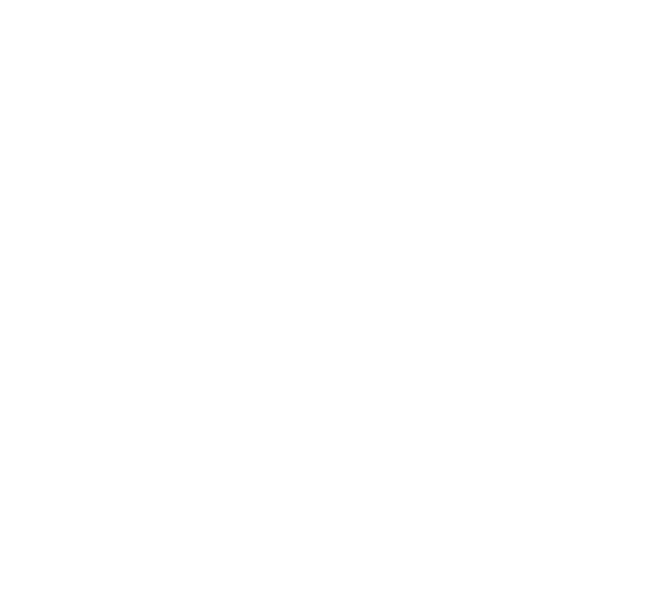
图为指挥家马里奥·帕奇
作曲家及杰出钢琴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特切列普宁深刻评价道,马里奥·帕奇大师的音乐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更承载着教育和传教的深远意义。在中国,梅百器大师被誉为“音乐大师”,他的每一次音乐活动都伴随着一个引人入胜的交响乐故事,以帮助听众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所演奏作品的内涵与魅力。梅百器大师不仅致力于演绎经典,更积极向听众推介中国和西欧当代作曲家的最新佳作。他常常超越同行的步伐,首次将这些作品带到中国观众的面前。正是因为梅百器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才得以领略到雷斯皮吉、拉威尔、柯达伊、巴托克、欣德米特等音乐巨匠的杰出作品。尽管当时的当局对这些曲目持保留态度,未能充分认识到其艺术价值,但梅百器始终坚定捍卫自己的观点,以他的专业精神、卓越表演技巧和国际声誉抵挡住了质疑之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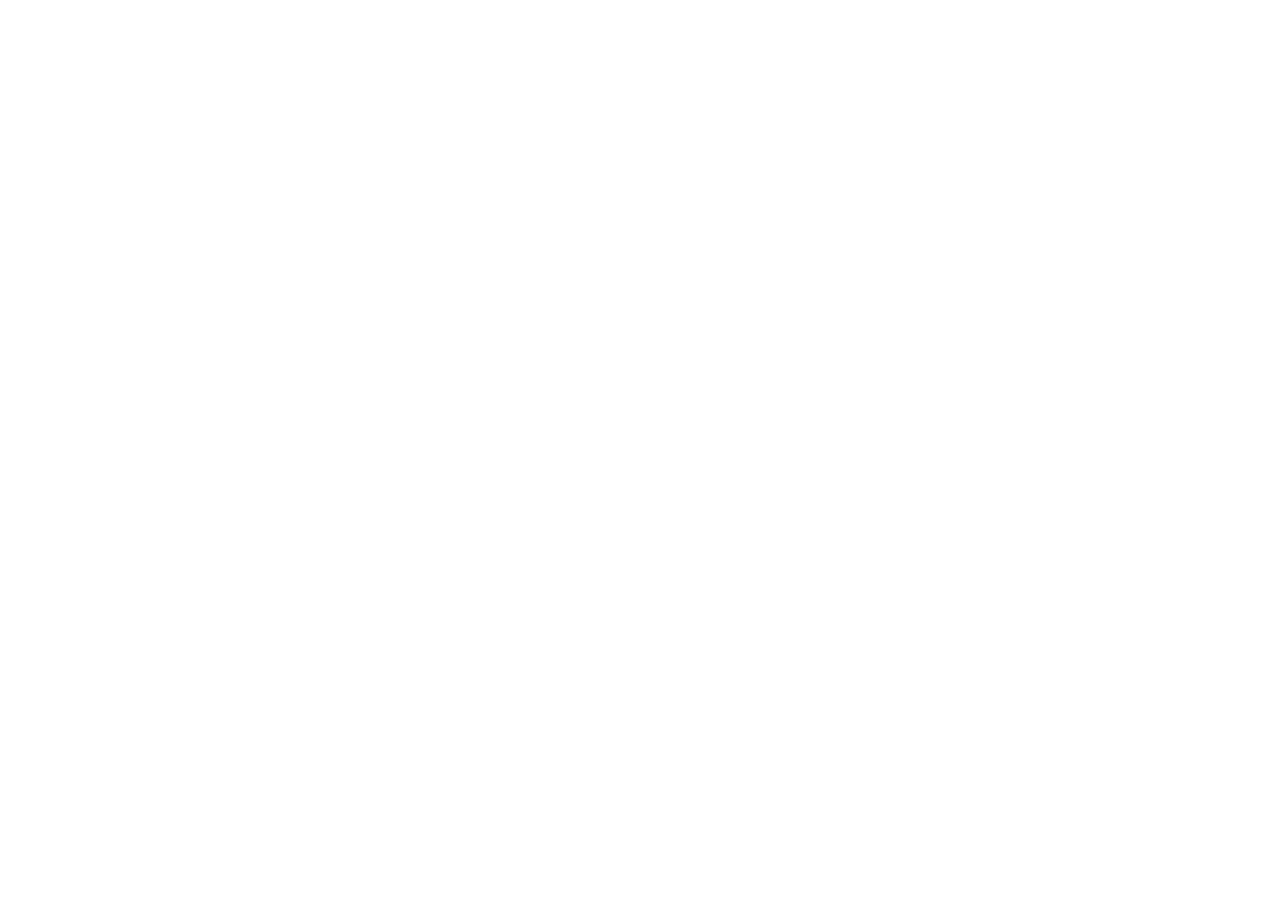
上海工部局乐队
谈及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历程,不得不提上海交响乐团这一东方音乐史上的璀璨明珠。它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音乐团体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乐团初创时期,由15名来自菲律宾的音乐家组成,并由法国长笛演奏家、作曲家及指挥家让·雷慕沙(1815-1880)担任指挥。这位来自法国的音乐家后来定居上海,为乐团注入了欧洲音乐的精髓。
随后,德国音乐家鲁道夫·巴克接任指挥一职。他从德国和奥地利引进了八名优秀音乐家,进一步提升了乐团的实力,并确立了定期排练和公开演出的制度。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克因被误解为协助德国军队而被驱逐出境,乐团一度失去了领导核心。
在这关键时刻,梅百器接过了指挥的接力棒,成为上海乐团的第三任指挥。乐团在市工商局的赞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其名称“工部上海交响乐团”也见证了这一历程。梅百器对乐团的建设充满热情与智慧,他在乐团首次试演(16 名欧洲人和 21 名菲律宾人)后便积极寻找新的音乐人才,邀请各类弦乐器和管乐器演奏者加入,甚至包括夜总会的音乐家。随后,他更是远赴欧洲,吸引了一批来自意大利、德国等国的专业音乐家加盟。在梅百器的精心组织下,乐团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演奏各种曲目的优秀交响乐团,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繁忙的音乐季中,梅百器大师不仅将音乐会场次从原先的20场扩充至令人瞩目的40场,更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室内乐音乐会、爵士乐音乐会以及青年音乐会。他创立并举办了多个独具特色的特别音乐节,为音乐爱好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梅百器大师在演出场地的选择上同样独具匠心,他乐于在任何能够容纳众多听众的音乐厅中表演,并始终致力于为观众创造最为舒适的观演环境。例如,允许观众在演出期间吸烟,以缓解长时间欣赏音乐可能带来的疲劳;同时,他还会用深色窗帘遮住窗户,以确保观众能够全神贯注地聚焦于台上精彩的演出,而不受外界光线的干扰。在夏日时,梅百器大师更是别出心裁地将音乐会移至公园和广场等露天场所举行,让市民们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能沉浸于美妙的音乐之中。
在制定音乐会演出计划时,梅百器大师始终深谙上海市民的多元化口味,他努力确保演出计划和演出质量能够尽可能接近西方大型交响乐团的顶级水平。这不仅体现在对曲目的精心挑选上,更体现在对演出细节的极致追求中。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城市,上海在各国代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下不断发展。梅百器大师紧紧围绕“国家主题”组织乐团的音乐会演出,如“法国音乐之夜”、“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等特色专题。在1923至1924年间,他成功举办了六场这样的音乐会,其中包括三场分别以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为主题的音乐之夜,以及两场俄罗斯音乐之夜。为了丰富乐团的曲库,梅百器还经常亲自前往意大利购买乐谱,甚至使用意大利大使馆的资金进行采购。
梅百器大师的音乐会节目鲜少重复,他每次都竭尽全力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以吸引更多的听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他希望打破人们对音乐的刻板印象,即认为音乐是昂贵的、是少数精英和富人的特权。因此,他的音乐会总是力求给社会各阶层的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曲目选择上,梅百器大师的品味既古典又现代。他既演绎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等欧洲古典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也积极推广和欣赏当代音乐以及二十世纪的“古典”风格作品。正是得益于他的卓越贡献,上海交响乐团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上海也因此成为了世界著名音乐家巡演的必经之地。众多高水平的专业演奏家和国际知名艺术家,如弗朗茨·克莱斯勒、阿瑟·鲁宾斯坦、亚沙·海菲兹、费奥多尔·恰利亚平、埃弗雷姆·齐姆巴利斯特以及约翰·麦克·科马克等,都曾与乐团携手合作,共同谱写了音乐史上的华彩篇章。
随后,德国音乐家鲁道夫·巴克接任指挥一职。他从德国和奥地利引进了八名优秀音乐家,进一步提升了乐团的实力,并确立了定期排练和公开演出的制度。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克因被误解为协助德国军队而被驱逐出境,乐团一度失去了领导核心。
在这关键时刻,梅百器接过了指挥的接力棒,成为上海乐团的第三任指挥。乐团在市工商局的赞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其名称“工部上海交响乐团”也见证了这一历程。梅百器对乐团的建设充满热情与智慧,他在乐团首次试演(16 名欧洲人和 21 名菲律宾人)后便积极寻找新的音乐人才,邀请各类弦乐器和管乐器演奏者加入,甚至包括夜总会的音乐家。随后,他更是远赴欧洲,吸引了一批来自意大利、德国等国的专业音乐家加盟。在梅百器的精心组织下,乐团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演奏各种曲目的优秀交响乐团,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繁忙的音乐季中,梅百器大师不仅将音乐会场次从原先的20场扩充至令人瞩目的40场,更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室内乐音乐会、爵士乐音乐会以及青年音乐会。他创立并举办了多个独具特色的特别音乐节,为音乐爱好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
梅百器大师在演出场地的选择上同样独具匠心,他乐于在任何能够容纳众多听众的音乐厅中表演,并始终致力于为观众创造最为舒适的观演环境。例如,允许观众在演出期间吸烟,以缓解长时间欣赏音乐可能带来的疲劳;同时,他还会用深色窗帘遮住窗户,以确保观众能够全神贯注地聚焦于台上精彩的演出,而不受外界光线的干扰。在夏日时,梅百器大师更是别出心裁地将音乐会移至公园和广场等露天场所举行,让市民们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能沉浸于美妙的音乐之中。
在制定音乐会演出计划时,梅百器大师始终深谙上海市民的多元化口味,他努力确保演出计划和演出质量能够尽可能接近西方大型交响乐团的顶级水平。这不仅体现在对曲目的精心挑选上,更体现在对演出细节的极致追求中。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城市,上海在各国代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下不断发展。梅百器大师紧紧围绕“国家主题”组织乐团的音乐会演出,如“法国音乐之夜”、“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等特色专题。在1923至1924年间,他成功举办了六场这样的音乐会,其中包括三场分别以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为主题的音乐之夜,以及两场俄罗斯音乐之夜。为了丰富乐团的曲库,梅百器还经常亲自前往意大利购买乐谱,甚至使用意大利大使馆的资金进行采购。
梅百器大师的音乐会节目鲜少重复,他每次都竭尽全力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以吸引更多的听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他希望打破人们对音乐的刻板印象,即认为音乐是昂贵的、是少数精英和富人的特权。因此,他的音乐会总是力求给社会各阶层的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曲目选择上,梅百器大师的品味既古典又现代。他既演绎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等欧洲古典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也积极推广和欣赏当代音乐以及二十世纪的“古典”风格作品。正是得益于他的卓越贡献,上海交响乐团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上海也因此成为了世界著名音乐家巡演的必经之地。众多高水平的专业演奏家和国际知名艺术家,如弗朗茨·克莱斯勒、阿瑟·鲁宾斯坦、亚沙·海菲兹、费奥多尔·恰利亚平、埃弗雷姆·齐姆巴利斯特以及约翰·麦克·科马克等,都曾与乐团携手合作,共同谱写了音乐史上的华彩篇章。
中国交响乐的形成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中国交响乐的形成时期。尽管当时中国作曲家的首部交响乐作品在艺术层面上尚显稚嫩,但它们的问世无疑成为了民族艺术史上一座意义非凡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交响乐创作的起始与觉醒。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0年11月23日注定成为了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光明大戏院,梅百器大师亲自执棒,指挥乐团完成了中国音乐家黄自的首部交响乐作品《思乡》的首演。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引发了观众的极大兴趣,收获了空前热烈的反响。而后的1935年12月18日,梅百器再度领衔,指挥合唱团与交响乐团联袂献上了中国作曲家张昊的杰出之作《民主胜利》。同年,交响乐团还倾情演绎了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并最终录制成了中国交响乐的首张唱片,成为了永恒的艺术珍品。
在上海度过的长达28年的岁月里,梅百器大师不仅在交响乐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业余时间致力于钢琴教育的普及与推广。他的许多学生都成为了后来在音乐领域的专业音乐家和教师,其中包括了董光光、傅聪、周广仁、巫漪丽、吴磊、杨嘉仁等一系列如雷贯耳的名字。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交响乐团开始跨界涉足电影配乐领域,展现了其多元的艺术魅力。1935年,乐团为电影《都市风光》精心谱写了《都市风光幻想曲》;1937年,他们又为电影《马路天使》创作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两部经典作品,均出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贺绿汀之手。值得一提的是,黄自为电影《都市风光》所创作的音乐录音,在梅百器的精湛指挥下由上海乐团完美呈现,并留存至今。这不仅是中国首部专为电影创作的器乐配乐,更是中国作曲家首部被录制成唱片的交响乐作品,标志着中国电影配乐艺术的新篇章。在此之前,中国电影大多使用作曲家为音乐会创作的音乐作品作为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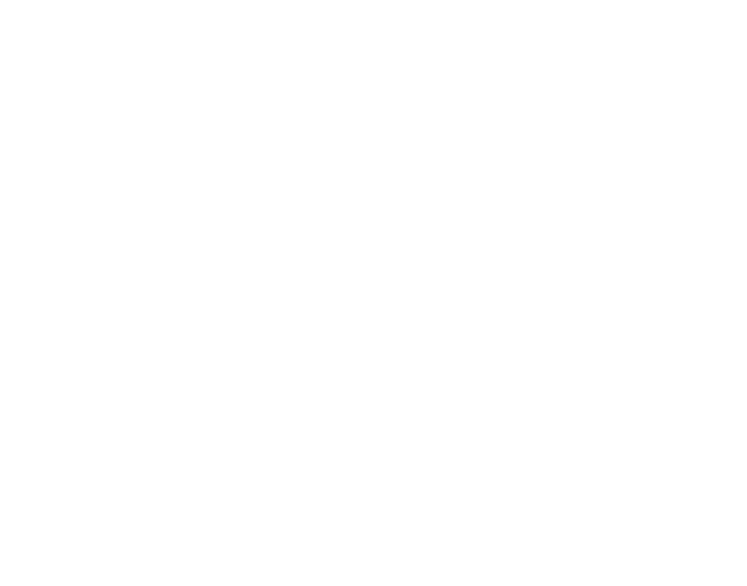
1945年6月,梅百器与学生在上海合影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曲折。1942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进驻,租界的文化生活遭到了严格的控制。上海市立交响乐团被迫更名为“上海爱乐乐团”。尽管侵略者希望梅百器能继续担任指挥,但这位坚韧不屈的意大利人却以拒绝合作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随后的四年里,梅百器将满腔热血投入到钢琴教育事业中,为众多中国音乐家提供了宝贵的私人钢琴课程。然而,1946年8月3日,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中风离世。
梅百器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普及西方古典音乐和发展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无可估量的。在他的影响与推动下,上海民族乐团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专业乐团,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复杂程度、风格和流派的音乐作品。乐团的成功也启发了中国的教育家们,他们在上海开办了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为后来的音乐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与平台。学生们在乐团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不断成长,毕业后更是成为了乐团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梅百器不仅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指挥家之一,更是中国交响乐艺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虽然上海交响乐团是在西欧国家的特许下成立的,但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左右民族交响乐的诞生与发展。他们认为,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音乐家创建的乐团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公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习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乐团成员在最初几乎全为外国人,后来虽然有两名中国音乐家加入,但外国交响乐团在当时的侵略国背景下工作,可能给民族文化带来了一些影响,但这些影响与中国交响乐本身的独立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
在随后的四年里,梅百器将满腔热血投入到钢琴教育事业中,为众多中国音乐家提供了宝贵的私人钢琴课程。然而,1946年8月3日,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中风离世。
梅百器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普及西方古典音乐和发展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无可估量的。在他的影响与推动下,上海民族乐团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专业乐团,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复杂程度、风格和流派的音乐作品。乐团的成功也启发了中国的教育家们,他们在上海开办了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为后来的音乐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与平台。学生们在乐团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不断成长,毕业后更是成为了乐团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梅百器不仅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指挥家之一,更是中国交响乐艺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虽然上海交响乐团是在西欧国家的特许下成立的,但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左右民族交响乐的诞生与发展。他们认为,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音乐家创建的乐团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公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习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乐团成员在最初几乎全为外国人,后来虽然有两名中国音乐家加入,但外国交响乐团在当时的侵略国背景下工作,可能给民族文化带来了一些影响,但这些影响与中国交响乐本身的独立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
交响乐实践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开始组织交响乐的排练。1940年,首都迁往重庆,上海、南京等地的音乐家也纷纷前往新首都。这些音乐家人数众多,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利用协会资金成立了“中国交响乐团”,并计划在抗战四周年之际举办一场爱国演出。这一计划引起了玉女观音乐厅音乐学院和重庆广播电台的关注。音乐学院和广播电台的领导也参与了交响乐团组织工作,在抗战纪念日当天,三支交响乐团同台演出,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很快,50多个小型定点乐团开始参加公开音乐会,以鼓舞民众。
抗战结束后,中华交响乐团回到南京。黎国荃被任命为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随后指挥一职由吴浩业担任。随着1948年国民党大败,中华交响乐团也撤退到广州。
在此期间,中国交响乐的创作开始起步。年轻有为的作曲家黄自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交响序曲《怀旧》。随后,江文也创作了管弦乐序曲《台湾舞曲》,冼星海创作了管弦乐作品《民族解放》和《神圣之战交响曲》,贺绿汀创作了管弦乐改编的民族旋律《森吉德玛》。
在战争年代的背景之下,作品无不流露出浓烈的爱国情感和创作力量的崛起。在这一特殊的时期,对于西欧音乐资源的深入理解和掌握显得尤为关键和深刻。管弦乐作品鲜明地展现了一种融合东西方音乐艺术精华的特色:它巧妙地将西方音乐艺术的严谨作曲规范与中国民族音乐独特的手法相融合,使得中国的优美旋律得以在西欧浪漫主义的和弦结构之中得以表现。音乐家们深感交响乐在表达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因此他们努力探索着如何将中西音乐元素完美融合,寻找出既能体现中国传统音乐韵味,又能展现西方音乐技巧的独特创作途径。
而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整个管弦乐运动的蓬勃发展。面对磨难与挑战的中国先进社会群体,深刻地意识到了管弦乐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在反映人民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戏剧性经历上的重要价值。因此,音乐家们纷纷致力于推动集体演出的兴起,并转向创作更为深刻、严肃的戏剧音乐作品。作曲家们更是在创作中积极寻求管弦乐与民族音乐内容的巧妙结合,以期创作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水准的杰出作品。
乐团功能的形成
1949至1957年间,管弦乐的创作空间日益宽广,想象力得以充分释放。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交响乐作曲家铺设了崭新的创作道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这一时期,中国作曲家们将管弦乐作品的焦点聚焦于生活题材与主题之上,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
马思聪的《山林之歌》、刘铁山 茅沅共同创作的《瑶族旋律》、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以及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等经典之作,都彰显了中国作曲家们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音乐形象的执着追求。这些作品中,原汁原味的民间旋律与曲调经过精心编配,与管弦乐的丰富色彩完美融合,既凸显了原创性,又赋予了作品新的艺术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管弦乐的声音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与民族音乐的和谐统一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风尚。人们开始积极探索如何以交响乐的方式驾驭民族音乐素材,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佳作。这一时期的管弦乐创作,无疑为中国音乐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音乐文化史上,1957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是由于中国政治形势造成的停滞期。在第一个十年(1957-1966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作曲家的交响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其他曾经飞速发展的中国艺术文化一样,交响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陷入了人为的停滞状态。在"卫星上天"和"冶金大跃进"口号的驱使下,艺术家们被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劳动。对于政治家而言,管弦乐团代表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贮备劳动力,可以用于农业生产,或者至少可以丰富农村的业余生活。
职业环境的动荡使“专注于艺术与政治的隔绝”的传统理念遭到挑战,而各式的排练和其他音乐活动也纷纷受到限制与约束。尽管如此,音乐家与作曲家们却仍旧坚韧地将个人命运与音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创作步伐,尽管遭遇重重阻碍,却并未完全停滞,而是在适应与妥协中寻求前行。
作曲家们纷纷强调交响乐的社会价值,以真实历史事件的深刻情节,佐证了交响作品在现实中的重大意义。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品更是通过对民族特色的强化与呈现,展现出音乐风格的多彩与独特。节目因素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意义。
从节目曲目的精心命名中,我们得以窥见作者们创作思想的深邃与缜密。军事爱国或民间题材的巧妙运用,使得这些作品在艰难时期更易于被大众接受与演绎。其中,王运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均堪称这一时期的典范之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以其细腻的旋律和生动的乐队色彩,成功捕捉了民间传说的神韵,成为当代中国节目音乐会交响乐的一张璀璨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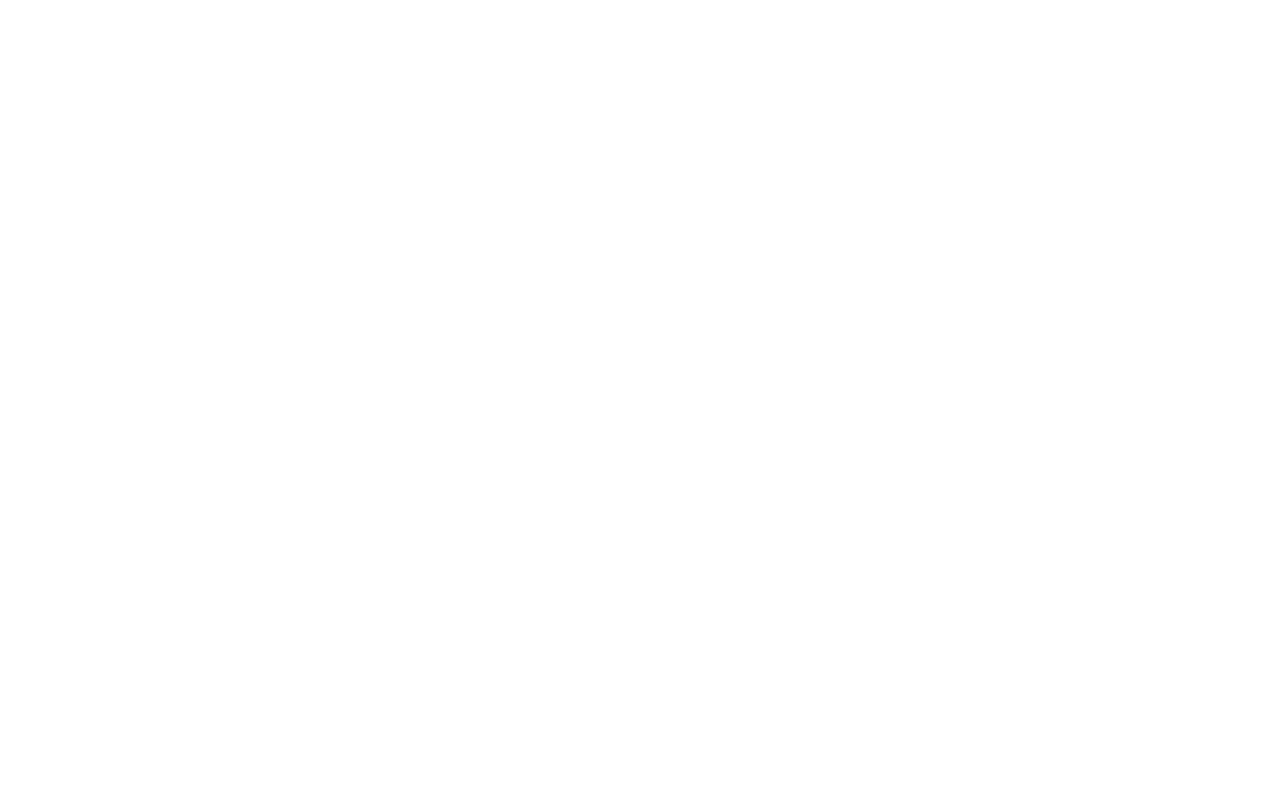
图为京剧演员在交响乐团的伴奏下表演。
《梨花颂》
演唱:万肖晨昱
京胡:宋瑞婷
《梨花颂》
演唱:万肖晨昱
京胡:宋瑞婷
京剧中的交响乐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十年中,中国的交响乐演奏家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歌剧。1965年1月,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访问中央乐团,此次访问如同一道分水岭,为作曲家交响乐作品的未来发展开启了全新的视角。她的意外造访以及对音乐家们管弦乐活动研究的积极参与,预示着一段崭新的篇章正徐徐展开。在江青的引领下,交响乐团全体成员齐心协力,投身于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的排练之中,并坚持要求交响乐团为该剧提供伴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提议,源于一位具有深厚影响力的高层人士,其推动力之强令人瞩目。
在领略了这部歌剧的魅力之后,李德伦迅速响应,力荐作曲家罗忠镕组建创作团队,以在短时间内创作出能够完美契合交响乐团伴奏的歌剧音乐会曲目。这一紧迫的创作任务推动了中国交响乐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意想不到的飞跃。
歌剧音乐会的改编实践极大地拓展了配器技巧,使得乐队首次全面融入到戏剧作品的情感表达之中。在管弦乐部分,听众得以聆听到对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以及在戏剧关键时刻所呈现出的极具张力的管弦乐表达。
如今,管弦乐在戏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创造了与剧情平行的表现力,用音乐语言深刻诠释了戏剧情境,进一步凸显了京剧体裁所固有的象征性和夸张效果。从中国戏剧与管弦乐的完美融合中,我们可以窥见文化艺术各领域间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交响乐艺术在汲取贝多芬、莫扎特等欧洲音乐巨匠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戏剧与交响乐之间的紧密关系,激发了对中国交响乐艺术的新一轮研究热潮。在交响乐版《沙家浜》成功首演之后不久,管弦乐序曲《智取威虎山》便应运而生,其主题内容充满了变革的力量:抒情的旋律主题散发出史诗般的音色,而尾声部分的戏剧氛围则巧妙地融入了舞蹈元素的灵动与韵律。
另一部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则展现出丰富的对比和层次。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充分展现了中国音乐家们难能可贵的品质——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高度一致使得个人的创作灵感得以相互激荡、倍增。这一趋势不仅赋予了中国戏剧文化更加丰富多元的发展动力,还使得不同艺术形式(如舞蹈、歌唱、杂技、表演等)之间得以相互借鉴、融合,共同将多种意义或意义的组成部分统一于一种更加和谐、完美的艺术形式之中。
开放的时代
自1979年起,中国踏入了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崭新的开放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交响乐终于挣脱了政治束缚的桎梏。交响乐作品由此成为中国作曲家们的创意资源,他们不仅熟稔西欧音乐语言的精髓与技巧,更深入地掌握了各类音乐形式与流派的内在规律。
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特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主体意识的显著增强。作曲家们开始更加鲜明地彰显个人风格与独特观念,他们的作品融入了自身对世界的深刻洞察与独特理解。同时,他们对民族音乐语言的领悟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新创作的交响乐作品无不透露出实现自我艺术理念与追求审美理想的强烈愿望。
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品层出不穷,如刘敦楠的小提琴与乐队组曲《山林》,谭盾的交响曲《李骚》,杜鸣心的小提琴与乐队协奏曲以及王西麟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这些作品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思想新体裁之间的和谐平衡。中国交响乐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裁和风格轮廓,既继承了传统音乐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创新元素。套曲原则和史诗抒情音乐模式的倾向与管弦乐体现的哲学深度和规模也实现了结合。
中国当代交响乐
最后一个阶段,但绝非是终点,这是一个开放且面向当代的阶段。其发端,恰恰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开放政策为重要的历史节点,现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为表演艺术团体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创作契机。交响乐团在过往没有专门的艺术领导,也缺乏规范的音乐季组织制度。然而,现在他们已能够自主制定节目单、选择曲目,并安排排练活动,乐团的运作也与音乐家的薪酬制度紧密相连,更加规范和合理。李德伦先生多次在音乐界中提及乐团运作方式的不足,并积极向国家领导人和文化部提出关于重建和优化乐团工作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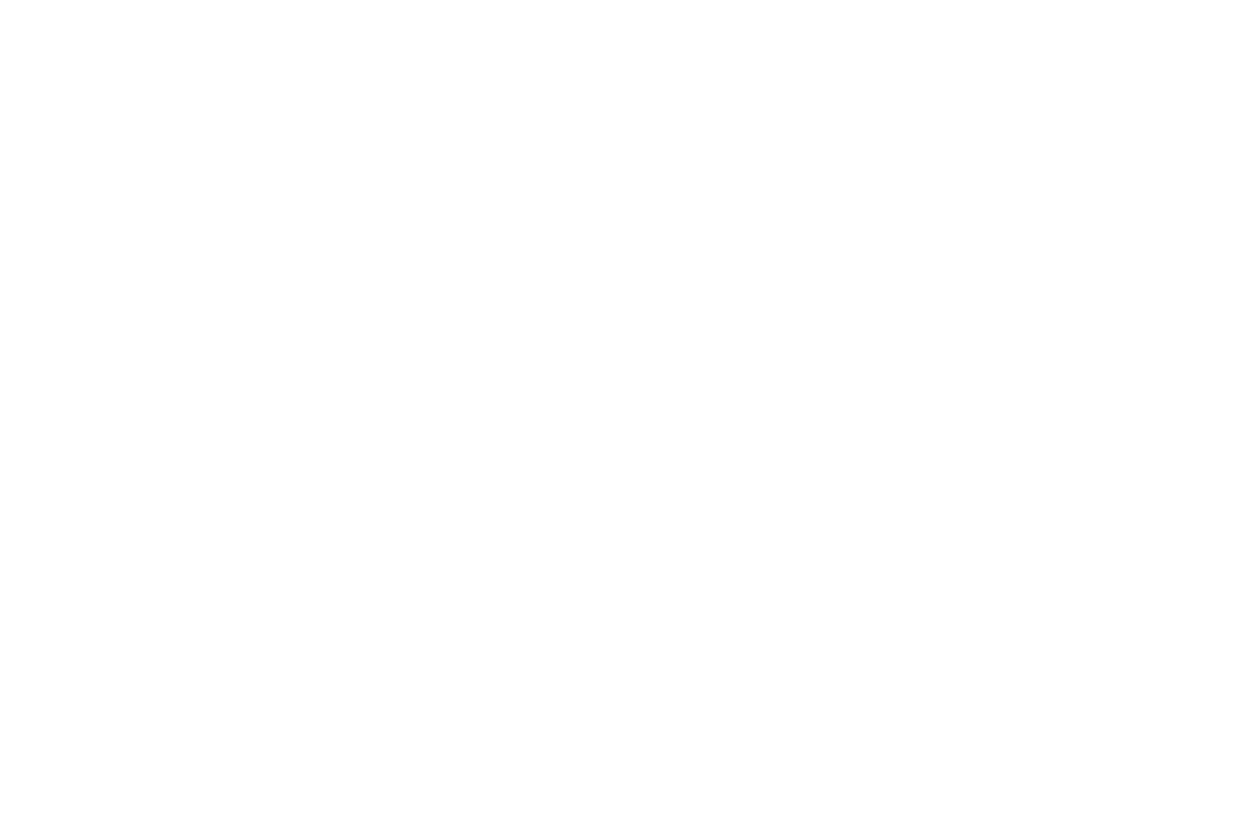
1957 年 4 月 2 日,李德伦在爱乐交响乐团大音乐厅的音乐会上
1996年,文化部对全国范围内的十二个交响乐团进行了深入改革,在原中央爱乐交响乐团的基础上,精心打造并组建了备受瞩目的中国交响乐团。鉴于李德伦先生在中国交响乐发展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及其在中国音乐文化界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文化部特别授予他指挥荣誉奖,以表彰他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卓越贡献。
1997年6月6日,李德伦先生的八十寿辰音乐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深情致敬,更是中国交响乐近年来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
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头十年,中国交响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全面反映了作曲家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祖国命运的密切关注以及对民族振兴的热切期盼。这些交响乐作品以其独特的戏剧视角,如同一部部抒情史诗或戏剧史诗,展现了人性的崇高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它们既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展现了儒学的哲学力度和当代人特有的敏锐感知力。
在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中,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百年沧桑》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佳作之一。这部作品延续了作曲家在第一部交响曲中探讨的“文革”悲剧性后果的主题,通过音乐语言深入剖析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影响。朱践耳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一个能够理解自己悲剧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的、自尊的民族。在困境中孕育着灿烂的明天。”
1997年6月6日,李德伦先生的八十寿辰音乐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深情致敬,更是中国交响乐近年来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示。
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头十年,中国交响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全面反映了作曲家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祖国命运的密切关注以及对民族振兴的热切期盼。这些交响乐作品以其独特的戏剧视角,如同一部部抒情史诗或戏剧史诗,展现了人性的崇高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它们既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感,又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展现了儒学的哲学力度和当代人特有的敏锐感知力。
在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中,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百年沧桑》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佳作之一。这部作品延续了作曲家在第一部交响曲中探讨的“文革”悲剧性后果的主题,通过音乐语言深入剖析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影响。朱践耳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一个能够理解自己悲剧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的、自尊的民族。在困境中孕育着灿烂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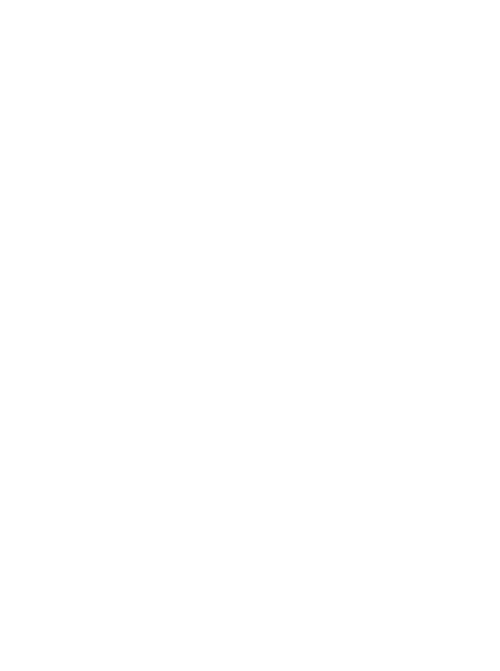
图为作曲家朱践耳
作曲家精心打造的《第二交响曲》深刻遵循心理发展的自然规律,巧妙融入“惊喜、悲伤、愤怒和力量”等多重情感元素。四个乐章间,音乐情绪如波浪般起伏跌宕,形成鲜明而富有张力的对比。
这部作品是作曲家以满腔热情献给藏族同胞的一份厚礼。1986年,他踏上西藏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立刻被其壮丽景色所震撼,更被其悠久而多彩的传统文化深深吸引。藏族音乐那质朴、神秘、肃穆而又欢快的艺术气质,令作曲家赞叹不已,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在《第二交响曲-百年沧桑》的第一乐章中,朱践耳以诗意的笔触写下了令人深思的纲领:“佛光还是阳光?在世间还是在天空?是昔日英勇的战鼓,还是新时代的脚步?历史犹如一部变幻莫测的长篇经文。”这部交响曲的史诗基调建立在发展变奏的原则之上,巧妙融合了民族旋律的丰富性、中国和声结构折射出的和声魅力,以及西方古典复调的技巧和序列原则。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管弦乐音乐语言的坚实基础,使中国交响乐在短短80多年的历史中,便迅速接近并比肩西方近300年积累的文化范式。
这部作品是作曲家以满腔热情献给藏族同胞的一份厚礼。1986年,他踏上西藏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立刻被其壮丽景色所震撼,更被其悠久而多彩的传统文化深深吸引。藏族音乐那质朴、神秘、肃穆而又欢快的艺术气质,令作曲家赞叹不已,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
在《第二交响曲-百年沧桑》的第一乐章中,朱践耳以诗意的笔触写下了令人深思的纲领:“佛光还是阳光?在世间还是在天空?是昔日英勇的战鼓,还是新时代的脚步?历史犹如一部变幻莫测的长篇经文。”这部交响曲的史诗基调建立在发展变奏的原则之上,巧妙融合了民族旋律的丰富性、中国和声结构折射出的和声魅力,以及西方古典复调的技巧和序列原则。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管弦乐音乐语言的坚实基础,使中国交响乐在短短80多年的历史中,便迅速接近并比肩西方近300年积累的文化范式。
结论
中国交响乐的发展与中国现代交响乐团的成长紧密相连,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今,全国22个省会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成为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股重要力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二线城市也开始考虑建立新的交响乐团,以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提升市民的艺术素养。
以张家界市为例,通过市政府的积极努力,2018年在张家界学院成功创立了爱乐乐团。这支乐团汇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客座外籍音乐家,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为乐团注入了新的活力。乐团的曲目丰富多样,包括中外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以及改编作品,为观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音乐体验。
2024年4月26日,乌克兰作曲家库库琴科·塔拉斯的交响诗《张家界大自然的力量》成功举行首演。这部作品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如同攀登高峰一般充满挑战与艰辛。然而,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与自然的力量重新连接,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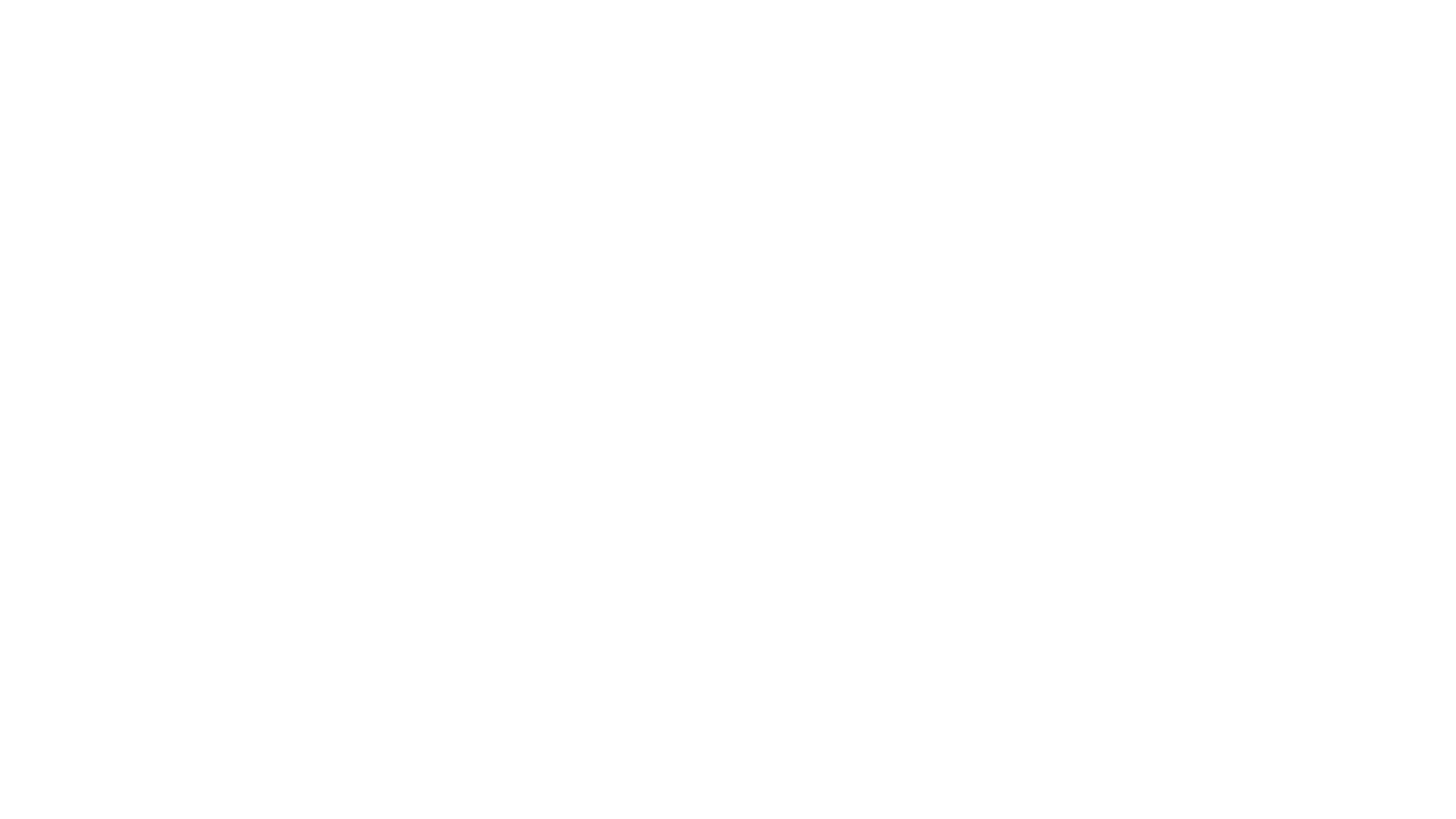
库岑科·塔拉斯和张家界爱乐乐团在交响诗《大自然的能量张家界》首演后,张家界大学音乐厅,2024 年 4 月 26 日。
展望未来,中国作曲家将继续秉持创作梦想,致力于创作出一部能够充分展现“中国现代民族气质和音乐水平,展现思想深度和对历史内涵的认识”的新交响乐作品。他们将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解,积极参与世界交响乐的创作。
资料来源清单
- 王繼和 中國現代音樂的簡史。 北京出版社,1991。 217 頁匡君.二十世纪中国民族管弦乐配器中的音色观念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 2008.
- 李涛.陈怡交响乐作品中的"多重结构"解读[J].上海音乐学院, 2010.
- 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 馬成 音樂和表演。 李大龍創作的中國交響樂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47 页
- 郝乃峰 關於一些當代作曲家的交響搜索。的上海: 現代中國出版社,2000。317 页史学军 凄美壮烈的民间史诗——民间交响组曲《乔家大院》赵季平//梅罗曼. 2008年4号 页面. 59–72)。
已读文章清单
1. 陆林.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马里奥·帕奇(梅百器)(1919-1942).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23-27 页.)(俄语)
2. 王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方法论支持(1937-1945).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2-4 页.)(俄语)
3. 任兴艳. 林耀基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其与世界其他教育体制的关系.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9-11 页.)(俄语)
4. 陈雁书. 中国甘肃省的传统民俗仪式.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43-45 页.)(俄语)
5. 努俊毅. 中国河南的小调曲种.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46-48 页.)(俄语)
2. 王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方法论支持(1937-1945).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2-4 页.)(俄语)
3. 任兴艳. 林耀基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其与世界其他教育体制的关系.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9-11 页.)(俄语)
4. 陈雁书. 中国甘肃省的传统民俗仪式.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43-45 页.)(俄语)
5. 努俊毅. 中国河南的小调曲种. 音乐教育与科学,第 1 期(14),2021 年,第 46-48 页.)(俄语)
作者简介:
库琴科·塔拉斯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获得音乐艺术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名誉教授。
张家界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法国巴黎国际首席指挥家协会会员。
美国伯克利音响工程师和编曲家协会会员。
国际仲裁协会会员。
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奖项获得者。
库琴科·塔拉斯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获得音乐艺术和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名誉教授。
张家界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法国巴黎国际首席指挥家协会会员。
美国伯克利音响工程师和编曲家协会会员。
国际仲裁协会会员。
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奖项获得者。
编辑团队
语言学博士 :马利民
张家界学院副校长 :袁启君
纽约大学哲学博士 :亚历克斯·西诺
语言学博士 :马利民
张家界学院副校长 :袁启君
纽约大学哲学博士 :亚历克斯·西诺